Seeking the Root of Folk Art: Analysis and Reflection on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engchong Jadeite Jade Carving
-
摘要:
腾冲的翡翠玉雕是在尊重天然翡翠原料物性的基础上,将古人的智慧和审美通过物化的过程所呈现出来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融合了腾冲先辈的生活经验和人文精神,富有时代的文化价值与工艺价值,在中国翡翠玉雕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以腾冲翡翠玉雕为研究对象,结合实地考察,试图通过“以人为本、以实用为中心;审曲面势、材美工巧;文饰与质朴统一;文化象征与隐喻的意象表达;模仿与创作的和谐共融”五个方面深入探讨腾冲翡翠玉雕造物的文化特征,以此揭示腾冲翡翠玉雕的造物传统理念,以期对当前时代背景下民间玉雕的造物实践与传承发展等方面的研究提供有意的视角和参考。
Abstract:Tengchong jadeite jade carving is a manifestation of the wisdom and aesthetics of the ancients through the process of materialization on the basis of respecting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of natural jadeite raw materials. It integrates the life experience and humanistic spirit of Tengchong's ancestors, and is rich in the cultural and technological values of the times.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jade carving. Taking Tengchong jadeite jade carvi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combined with relevant field investigations, this study attempts to deeply explore the cultural features of creation of Tengchong jadeite jade carving from five aspects: "people-oriented and practical as the center, reviewing the situation, beautiful materials and exquisite workmanship, the unity of decoration and simplicity, the image expression of cultural symbols and metaphors, and the harmonious integration of imitation and creation". This reveals the creation tradition of Tengchong jade carving. I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a meaningful perspective for the research on the creation practic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folk jade carving in the current era.
-
Keywords:
- jade carving /
- creation /
- cultural feature /
- Tengchong, Yunnan Province, China
-
1. 造物的相关概念
中国传统造物是内嵌在民众生活习惯中的情感经验与精神创造,是发现和认识中华民族特征和审美意识的物化呈现。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中提到关于制造和思想的关系,“关于制造过程,一部分为思想,一部分为制作,起点和形式是由思想进行的,从思想末一步再进行的功夫为制作”[1],其观点强调了制造过程中技艺与思想的重要性。潘鲁生在研究中曾提到张道一先生的“造物艺术论”,将造物艺术放在本元文化的高度来考察,认为造物是人类最基本的一种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显现,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结合,保留了“造物”一词在历史上所包含的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含义, 即“造物在人类主动改造自然事物的实践中,不仅是人类对技术、材料、工艺、造型的物态化创造,其背后呈现的是人类创造实践过程中的精神内涵,因此,造物体现了人与物的本质关系,也体现了先民在生活实践中对待外物的精神态度。”[2]本文中的造物不仅是一种以装饰、美化、实用为功能的物化劳动产品,同时也是一种表达精神气质的美学活动和艺术行为,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与哲理。
腾冲翡翠玉雕至今已有500余年的历史,主要以缅甸翡翠为原料,其艺术风格融合了北派和南派玉雕中浑厚沉稳、儒雅灵秀的特点以及至真至朴的本土文化特色,被当地命名为“滇派玉雕”。作为一种扎根于乡土社会的民间艺术,腾冲翡翠玉雕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的产生与发展受到一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如造物过程中的造物原则、造物特征、技艺水平以及社会文明等诸多因素,这些因素承载着丰富的传统造物观念和价值理念,并且在腾冲翡翠玉雕造物历程中具有极其珍贵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张道一将传统艺术分为民间、宫廷、文人和宗教四种艺术类型,并认为民间艺术是建构艺术学理论体系影响最深的类型[3]。他把民间艺术理解为一切艺术的土壤和源泉,称之为“艺术的原生态”“本原艺术”或者“母体艺术”,并完整引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中的一段话:“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其核心思想被简括为“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4],以此强调了民间艺术的重要性。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不应只重点关注那些精英文化或是宫廷文化,那些代表平凡大众的民间文化也是最为鲜活和最具有生命力的代表。正如根植于民间社会的腾冲翡翠玉雕,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不仅是中国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腾冲社会母体艺术的造物特征,同时也是当地艺术文化创作的主要土壤和动力,但由于腾冲社会民间文化的质朴性、真实性和乡土性,在长期的浸染和沉淀的背景下,赋予了腾冲翡翠玉雕朴素无华、沉稳厚重的审美理想和造物特征。本文将以腾冲翡翠玉雕作为物质载体,以此探究其背后的造物传统以及所蕴含的精神文化内涵,以期为腾冲翡翠玉雕设计理论的形成提供些许参考与范式。
2. 腾冲翡翠玉雕的造物文化特征
2.1 以人为本,以实用为中心
在中国传统造物中,造型设计、制造工艺、制作规范等要素基本是建立在以人为本,适合人们所用的原则基础之上。其中,以诸子中墨子、韩非子、管子等为代表,均极力主张“以人为本,实用为中心”的造物观,即人本思想,以人为本的实用理性精神,旨在主张造物为大众服务,满足大众的物质需求,并符合人们心中的尺度。正如柳宗悦先生关于工艺文化的阐述:“材料是天籁,其中凝缩了许多人工智慧难以预料的神秘因素,需要根据材料的物理特性来确定用途,施加合适的工艺,才能使器物具有优良的功能。美和用结合的产物就是工艺,工艺之用即工艺之美和服务之美,如坚实的品质,准确的形状,沉静的色彩,这些保证了美的形制,为生活用途而服务,则是工艺的精神。”[5]因此,在腾冲翡翠玉雕造物过程中,最大限度的保留玉料的原形、原色,以致用和惜物的理念制作出符合人们功用与尺度标准的物品是较为重要的造物原则。
所谓“尺度”,通常是指器物的造型根据人的实用需求、生理特点以及气质意志所形成的恰当合理的尺寸和比例范围。器物造型的尺度,受到一定功能的制约。在腾冲翡翠玉雕造物中,翡翠挂件、摆件、手镯等不同品类的物品都有相关的用材标准,一般秉承“美玉不琢,不琢或少琢,取其天然,服务大众”的节用原则。因材料的特性不同,用途也不尽相同,如在下料之前需要先观察玉料,如玉料颜色均匀,可顺着玉料的裂纹切开,对其进行设计制作为手镯、圆珠、戒面、器皿等;如切开的玉材中有绺裂,一般雕刻花鸟或者山水题材的摆件或挂件,这样有利于通过镂雕或巧雕的形式挖脏去绺或反瑕为瑜,使材料各尽其用。翡翠挂件为了便于佩带和视觉美观,其厚度需根据切开的玉料品质来进行判断和确定。一般普通材质的挂件厚度为0.4~0.7 cm,若材质种水、色泽都相对较好,其厚度可保留至1.0 cm。若料越薄,越容易体现较好的透水效果;若料过厚,就会因透明度较差而使色泽沉闷影响视觉感官。因此,把握料的尺度尤其关键。此外,在腾冲翡翠玉雕挂件中,观音、佛像、生肖、守护神等造型题材备受青睐,这可能与人们的信仰和意念有关,人们以此祈愿事业蒸蒸日上,富贵平安等,这是从精神层面来体现“以人为本,以实用为中心”的尺度标准。在腾冲翡翠玉雕中,艺人在原料、题材、造型以及尺寸的设计加工时,多考虑到佩戴者的不同气质和意念等因素,既注重物的实用性又注重人的精神追求,以此来表达现代人体工学和设计心理学的精髓。正如高丰在《美的造物》一书中论述:“对兵器的设计制作,也要以符合人的尺度,适合人所用作为标准。他以制弓为例,认为制弓不仅要依据人的体形,且要因人的意志、血性、气质而异。长得矮胖,意念宽缓,行动舒迟的人,要为他制作强劲、急疾的弓以及柔缓的箭来配合使用。而刚毅果敢,行动急疾的人,要替他制作柔软的弓和急疾的箭加以配合。”[6]在这里,尺度是建立人与物之间关系的重要媒介,尤其当物与人的身体和情感建立密切的联系时,物的审美就不仅是通过视觉感官,而是通过触觉感、运动感或精神愉悦感进行回应。
腾冲翡翠博物馆传统翡翠纽扣(图 1和图 2)造型较为丰富,主要以四方形、圆形、多边形等不同几何形制为主,倾向于朴实无华的素面工艺和欧洲刻面切割工艺,通过直线和曲线,以曲直相依的形式形成内圆外圆、内圆外方或外方内圆等不同的造型,其形态规整对称,造型简约大方。中间薄,边缘厚的表现形式减轻了纽扣本身的体量感和厚重感,增强了佩戴的轻适性。部分刻面纽扣中间用金属做纽,增强了其耐磨性和装饰性。纽扣除御寒保暖外的实用性以外,且具有一定的装饰效果,也体现了“天圆地方”的朴素造物观念。天圆地方阐述了方与圆的辩证关系,即“方者,地之阔,圆者,天之阔。天地之道实乃方圆之道,方圆共体,是大自然的真理,也是中华文化的根本”[7]。在这里,天圆地方是指腾冲翡翠玉雕纽扣的造型“方中造圆,圆中制方”的雕刻技法,时刻提醒人们为人处事要有圆融、智慧、方法和态度,心中需要遵循方正守矩,坚守有圆有方,方可成事的因果定律。这些不仅重视人类现实生命文化精神,又注重实用和装饰为一体的翡翠纽扣,正是在“以人为本,以实用为中心”的造物原则下设计出来的。
2.2 审曲面势,材美工巧
《考工记》中大量论述了材料工艺制作技术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辩民器,谓之百工,材美工巧。”[8]其中,审曲面势主要从材料本身出发,深入审视和体察自然物材的形状、质地、肌理、色彩和光泽等物理性能以及造物的内容、形式、功能等关系,通过严谨的构思设计,依据材料的自然特性,施加人工,制为器物,强调了玉雕技艺的审美标准与材料、自然的关系。材美工巧是指对材料质地品性的选择,要求工匠主动去认识材料的物性,具体到某一器物的制作,涉及合理的选材用材[9]。它是体现自然造化最为直观、有效的手段和方法,即尊重玉材的本质,不强制利用人为外力去破坏其天然美感,遵循自然律和顺应自然物的同时,合理地选材用材。在此,“工巧”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做工的精良和高超的技艺;二是好的意匠,即一种规划、设想、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以及创造力,是工匠对材料、工艺、造型的整体考虑[10]。在翡翠玉雕造物中,有一种常用的特殊雕刻工艺被称之为“俏色巧雕”。因每块翡翠原料都有不同的自然形态,根据其质地、肌理、色彩等元素进行合理地选材以及主次关系构思设计,尤其是巧妙利用翡翠原石的皮色、本体色、内含物色等特点进行巧雕,使原料得到充分地利用与发挥,最终通过题材、造型、寓意的表达达到天工与人工的均衡统一,这是翡翠玉雕区别于其它玉石雕刻的特性之一。
以树明玉雕工作室作品《自在罗汉》(图 3)为例,作品材质为三彩翡翠,主体颜色偏青绿色,质地较好。在选料的构思环节初期,匠人根据原料的色彩分布、质地和纹理,拟将其设计为山水题材摆件,但在挫型过程中,原料内部出现大量的白色絮状物和颗粒棉点,于是艺人重整构思,将其改雕为人物题材。在尊重自然材料的前提下,秉承“审曲面势、材美工巧”的造物原则,结合挖脏去绺的表现方法,以及色彩的差异,雕刻主体设计成罗汉。通过镂雕工艺,利用内含物俏色巧雕的技法除去多余的白色棉点和絮状物,仅保留了罗汉手中持有的一颗白色“智珠”,以此表现罗汉与灵蟾、灵兽戏耍,悠哉乐哉的生活态度。黄色皮壳雕刻为金蟾,通过亮光和亚光相结合的抛光方式,塑造了鲜活的人物形象,既有古朴之意,又增强了玉雕作品的层次感。此件作品充分释放了玉材的天性,利用玉料的自然形态、质地、色彩和纹理,随形就势、因料施艺及去瑕显瑜的表现形式将翡翠原料转化为理想的器物,塑造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形象符号, 体现了工与物的完美融合,即所谓的“天工意匠”。
又如树明玉雕工作室作品《鱼龙》(图 4),整块原料为冰底黄翡,形扁长,经过长期地构思琢磨,匠人将冰底部分的原料以线刻和浮雕的形式雕刻为波涛,黄翡则雕刻为龙头鱼身,展示了鱼龙非凡的抱负和豪迈的气概,同时也寓意着“鱼跃龙门”的美好祝愿。整件作品以“俏色巧雕、因材施艺”的表现技法将原料刻画成鱼龙的形态,既保持了原料的完整性,又发挥原料的价值,更好地体现了“审曲面势,材美工巧”的造物理念。
2.3 质朴与文饰的相互统一
文与质的统一即文质彬彬,是中国传统工艺思想的美学核心。《论语·雍也》中,孔子用“文”与“质”来形容君子,“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该句原意是指人的道德和修养,强调人的内在道德修养与外在气质相一致。从工艺的角度来说,“文”是指文辞上的修饰,引申到器物是指器物的题材、造型、色彩、纹样、装饰等艺术元素,即物的外在表现形式,体现为装饰美。“质”是指道德品质,延伸到器物是指材料本身、材料性能以及器物的功利实用价值[11]。腾冲传统翡翠玉雕主要体现了玉材与器物的题材、造型、纹样、功能等内容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形式是内容诸多要素的结构方式和表现形态,是事物的外观;内容是构成事物内在要素的综合,是事物的本质方面。也就是说,在玉雕造物过程中,文与质合的工艺原则主要表现为形式与内容的相互统一,如果质朴胜过文饰就会显得粗犷,文饰胜过质朴就会感觉虚空,质朴与文饰应均衡统一。正如黑格尔[12]所说:“形式与内容是成对的规定,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
以腾冲艺盛和翡翠作品《冰心壶》(图 5)为例,题材来源于诗词“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冰和玉,古人常以之象征美德,希望通过玉壶的冰清玉洁和气度非凡品质比喻品德高尚、清廉的人。冰心壶以一块完整的冰种绿底翡翠为原料雕刻完成,其质地细腻,结构紧致,色彩分布均匀,透明度较好。艺人按照,壶体的黄金比例和严格的尺寸大小,经过对不同构件地设计与雕刻,采用传统的掏膛技术制作壶身与壶嘴,运用以活链技术连接壶盖与壶身,简约地雕刻与修饰壶体表面,并结合亮光的抛光方法展现了壶体晶莹剔透的感觉,蕴含着腾冲边民质朴无华的精神气质。首先,科学地设计与制作不仅满足了器物的实用性,如防止壶盖与壶身分离体现了质的内容;其次,活链技术、借料补空的表现手法以及简单的纹理雕刻增强了器物的体量感、立体感和装饰感,呈现了文饰外在形式的装饰美。在此,文饰与质朴相互统一的工艺原则在以玉材为载体的器物中得以淋漓尽致地体现,题材、造型、纹样、装饰等形式美元素完美地服务于器物功能的需要,即“装饰与功能,形式与内容”在器物中寻求到平衡统一的关系。
![]() 图 5 杨儒翡翠玉雕作品《冰心壶》(腾冲艺盛和翡翠)[12]Figure 5. Ice Pot by Yang Ru (Tengchong Yishenghe Jadeite)
图 5 杨儒翡翠玉雕作品《冰心壶》(腾冲艺盛和翡翠)[12]Figure 5. Ice Pot by Yang Ru (Tengchong Yishenghe Jadeite)2.4 文化象征与隐喻的意象表达
文化象征与隐喻的意象表达隐藏着视觉形象以外的深层含义,玉雕物化的过程包含了创作者的思维情感、信仰观念、生活经验以及审美理想。玉雕创作中的象征和隐喻由诸多要素构成,创作的题材、物象的形态、玉料的色彩以及物象的谐音等均可象征和隐喻不同文化的内涵寓意,暗喻形象之外的情感经验和文化行为,但需要符合物用的感官愉悦、伦理道德的感化以及审美情感的满足。在腾冲翡翠玉雕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文化象征与隐喻的意象表达作为文化思想重要的内在规定性,其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和文化要素亘古不变。艺人们善于从充满生机的自然界中获取灵感,如生生不息的山川草木、日月星辰、飞鸟走兽等题材都是创作的来源,这些自然元素均有独特的文化象征和精神隐喻,通常引申为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寄寓对某种情感的寄托和期望。
鹿被誉为吉祥如意、福禄长寿和财运旺盛的象征, 腾越工匠树明玉雕工作室作品《遇见》(图 6),作品以鹿为题材,利用独特的雪花棉翡翠,以线条和块面的形式对鹿的头部造型进行高度凝练和简约刻画,通过写实和写意的手法,传达雪花场景下鹿与人的遇见,隐喻着作者对未来美好的期许。
莲象征着出淤泥而不染,且与“廉”谐音,以此象征和隐喻为人正直、清廉、圣洁的品格和美德。腾冲传统翡翠帽饰《一品清廉》(图 7)以莲叶和莲花为题材纹样, 传统翡翠帽饰《一路连科》(图 8),玉料质地纯净,题材纹样借助了白鹭与莲叶,莲叶代表纯洁,鹭与路,莲与连均是谐音,代表吉祥如意,寓意仕途顺利,一路攀升,象征一种坚韧勇敢的品格以及智慧的生活态度。通过物象谐音、借材寓意等方法来表达文化思想是一种视觉形象以外深层含义和情感经验的映射和延伸,同时也是腾冲翡翠玉雕工艺一直遵循的传统造物原则,这种“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表达图式深刻地迎合了大众社会的价值取向和思想观念。
此外,腾冲玉雕作为一种根植于土壤的母型文化,流露着草根社会的主体力量,匠人虽然没有接受专业的训练,但在当代社会潮流中主动了解西方古典主义以及中国当代审美意象特征,以人类文明的反思为起点,儒家人伦秩序“仁、义、礼、智、信”为文化核心,生活感知和行为经验为主线,逐渐进入到批判人类生存现实状态的精神领域。腾冲翡翠玉雕造物没有刻意地追求当下主流创作的题材与样式,没有永恒不变地接受传统的观念与表现形式,而是通过特立独行的艺术活动伴随当地人民的信仰习俗、自身的经验感知、审美思考和精神动力来观照自然与人类生活的嬗变,同时在解构传统的艺术意象中对当今社会现实和人文精神进行反映与鞭笞,以此超越和反观传统的玉雕表现形式。树明玉雕工作室的作品《在世佛》(图 9) 获选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举办的2022年云南省首届“非遗伴手礼”。此作品源于一位女孩给妈妈订制的生日礼物,围绕“父母本是在世佛,何须千里拜灵山”典故进行艺术创作。匠人利用糯冰种翡翠原料,以简洁的传统佛像造型和现代人物形象通过人物空间关系的组合与虚实对比,将传统的造物题材、造物思想用现代设计的理念进行意象地表达,希望引发在当今浮躁的社会里,人们对于父母亲情、伦理孝道等系列现实问题的思考与重构。在此,腾冲翡翠玉雕文化和普适的社会价值观建立起了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秩序,物品世界与人的精神世界也因此建立了一种内在的联系。翡翠玉雕以“物”的形式凝聚了多重人格与文化语义,通过隐喻和象征的意象表达,来修正和规范现实社会中人格品性与道德修为,这种秩序与联系正好回应了工业文明以后人类心灵迷失的现时状态。
2.5 创造与模仿的和谐共融
腾冲翡翠玉雕没有形成系统的传承模式,艺人们均经历了长期学习,具备扎实的雕刻基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文化自觉意识,掌握了较为全面的工艺技法与技巧。在工艺传承的过程中,艺人们虽然文化水平不高,未受过专业的玉雕绘画训练,他们的造物视野常局限于熟悉的生活环境和有限的知识中,作品几乎包含了生活的经历以及审美经验的再现,他们的学习过程不是单一时间段内简单的观察和绘画,而是长期融入于现实生活中的学习体悟, 其难以量化,带有时空的多维性与情感的复杂性;其次是模仿。玉雕艺人们通过观察形成经验认知,在边看边学的过程中自觉与不自觉地对传统玉雕纹样和实物进行模仿,通过对“物”的模仿达到“形似”与“神似”,其纹样素材主要源于中国传统玉雕图案和市场文玩器物造型。这种模仿实践主要是通过有意识地记录和观察,形成记忆并借助纸质媒介对认知的图像进行记录模仿,这种模仿是一种长期的结果;再次是融会。这个过程需要结合翡翠原料的天然特性和传承人的知识技能,通过转化和移植的方法实现。在物化过程中,有时艺人们需要根据翡翠原料的物性避开绺裂和矿物杂质,进行玉雕造型的修正和二度创造,有时需要在造型模仿的基础上,结合深厚的技术经验和审美情趣,融入一些自己的理解和习惯性的表现方式,通过个人思考和情感体验有所突破和创造,即在传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玉雕风格,所以这种玉雕创作既是个人的,但又往往具有集体的、无意识的行为色彩。正如亚里士多德对于艺术本质的理解中提到“艺术最大的规律特征或者内在本质在于模仿,人类的艺术活动就是一种认识、实践与创造的过程”[13]。总之,器物和图案的经验性观察与模仿的技术行为成为腾冲翡翠玉雕创造的基础和关键,即观察、模仿与创造形成了玉雕艺人共同的艺术行为,并且之间形成一种和谐共融的关系,或许这也是民间传统工艺共同存在的一种创造行为方式和艺术范本。
腾越工匠树明玉雕《宝宝佛》系列(图 10)在模仿中国传统佛教题材的基础上,结合当前时代的审美趣味,将人物造型以夸张和风趣的卡通形象进行了二度创作。创作的内容与其模仿的原内容已有所不同,这意味着原作的原真性、艺术家的创造性等规则的解构和重组,在经历创造与模仿之后的腾冲翡翠玉雕造就了一种置于实践关系里的活态艺术本体和融于日常生活的修正创作观。对此,腾冲的翡翠玉雕艺术不仅仅是固态的,其创造结果也是一种持续模仿、再练习、再生产、再修正、再创造的结果[14]。
总之,腾冲的翡翠玉雕造物始终立足于对日常生活与周边事物的感知和隐性的观察,是一个凭借生活经验、自觉意识以及想象维度在长期的模仿与工艺实践中不断反复琢磨、积累与物化的过程。玉雕艺人们通过脑海中生成的系列符号系统,形成了相关的创造心理和行为经验,促使利于社会发展的个性精神得到自由彰显。尤其人作为传承主体,在模仿和创造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得以自我改造与完善,人的本质力量得以一定的突显,人的创造能力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15]。这种成功是一种创作本能和个体创造,一种自我意识和自我价值得以实现并且充满人性的活动与过程,也是一种民族文化价值的认同与复归。
3. 结语
本文围绕“以人为本,以实用为中心;审曲面势,材美工巧;质朴与文饰相互统一;文化象征与隐喻的意象表达;模仿与创造的和谐共融”五个方面的内容探讨了腾冲翡翠玉雕的造物特征。不仅是为了挖掘腾冲翡翠玉雕造物的传统文化, 同时也是为多元文化背景下,民间玉雕的造物实践与传承发展提供相关的创作参考和借鉴。
腾冲翡翠玉雕是在尊重玉材天性的基础上,通过艺人高超的雕刻技艺,融合古代人的审美态度、文化观念和造物智慧而形成的一种艺术形式,在数百年的历史绵延过程中,有着其自身存续和发展的内在逻辑,原因是固有的传统工艺已经形成造物规律和造物原则的程式化,以及系列的地方性知识和技术经验,这种蕴藏于实践和经验之中不易习得的知识、规律和原则,构成了其稳定的传承内在延续力,这不仅是玉雕匠人对于先民传统造物思想的参照与借鉴,也是对于本土传统民间文化的延续与再造,其造物的审美意识和主流思想不仅体现着腾冲翡翠玉雕与中国农耕文化的一脉相承,也呈现了腾冲的民族色彩和地方观念。更重要的是,匠人们始终以常然的态度,在自然与人为,天工与人工之间寻找着一种平衡和谐的关系,并通过腾冲翡翠玉雕造物得以彰显,以此映射出人与自然、人与物、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致谢: 衷心感谢腾冲树明玉雕工作室、艺盛和翡翠以及腾冲翡翠博物馆为此文提供了部分作品图片以及对相关调研工作的大力支持! -
图 5 杨儒翡翠玉雕作品《冰心壶》(腾冲艺盛和翡翠)[12]
Figure 5. Ice Pot by Yang Ru (Tengchong Yishenghe Jadeite)
-
[1] 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M]. 吴寿彭,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1: 137. Aristotle. Metaphysics[M]. Wu P S, translated.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1991: 137. (in Chinese)
[2] 潘鲁生. 论中华传统造物艺术体系的研究意义[J]. 艺术设计研究, 2021(2): 57. Pan L 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esearch on the system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reation art[J]. Art & Design Research, 2021(2): 57. (in Chinese)
[3] 李倍雷. 中国民间艺术在史学中的价值与意义[J]. 艺术百家, 2014(5): 105. Li B L.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folk art in history[J]. Hundred Schools in Arts, 2014(5): 105. (in Chinese)
[4] 陈岸瑛. 传统与现代经典艺术形象的生成机制与"统一场"理论的可能[J]. 艺术学研究, 2021(6): 34-44. Chen A Y.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traditional and modern classic art image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the "unified field" theory[J]. Chinese Journal of Art Studies, 2021(6): 34-44. (in Chinese)
[5] (日)柳宗悦. 工艺之道[M].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9: 16-17. (Japan) Sooetsu Yanagi. Way of craftsmanship[M]. Beijing: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2019: 16-17. (in Chinese)
[6] 高丰. 美的造物——艺术设计历史与理论文集[M]. 北京: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2004: 167, 170-171. Gao F. Beautiful Creation——Collections of art design history and theory[M]. Beijing: Beijing Arts and Crafts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2004: 167, 170-171. (in Chinese)
[7] 牛晓霆. 匠艺寻根: 对明式家具造型美本体的剖析与思考[J]. 艺术设计研究, 2022(3): 83. Niu X T. Seeking the roots of craftsmanship: Analysis and reflection on the ontology beauty of Ming-style furniture[J]. Art & Design Research, 2022(3): 83. (in Chinese)
[8] 孙璐. 扬州玉雕的造物文化思想研究[J]. 艺术百家, 2015, 31(5): 250-251. doi: 10.3969/j.issn.1003-9104.2015.05.050 Sun L. Cultural thought of Yangzhou jade carving[J]. Hundred Schools in Arts, 2015, 31(5): 250-251. (in Chinese) doi: 10.3969/j.issn.1003-9104.2015.05.050
[9] 乔臻. 以中国传统造物观念审视现代设计的技术美[J]. 黑龙江史志, 2008(18): 48. Qiao Z. Examining the technical beauty of modern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reativity[J]. Historical Records of Heilongjiang, 2008(18): 48. (in Chinese)
[10] 姜坤鹏. 物我合一: 传统琢玉工艺审美研究[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21: 155. Jiang K P. Object and man in one aesthetic research on the traditional jade carving[M].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2021: 155. (in Chinese)
[11] Wang W W, Lu R. Research on features and applications of jadeite products in Tengchong, China[J]. Journal of Gems & Gemmology, 2023, 25(115): 81-88.
[12] 黑格尔. 小逻辑[M]. 贺麟, 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80: 279. Hegel. Shorter logic[M]. He L, translated.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1980: 279. (in Chinese)
[13] 张月萍. 珠宝美学[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0: 73. Zhang Y P. Jewelry aesthetics[M].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20: 73. (in Chinese)
[14] 薛其龙. 创作与复制: 傈僳族农民画家的实践模式[J]. 民族艺术, 2021(5): 149-157. Xue Q L. Creation and reproduction: The practical model of lisu farmer painters[J]. Ethnic Arts Quarterly, 2021(5): 149-157. (in Chinese)
[15] 诸葛铠. "造物艺术论"的学术价值[J]. 山东社会科学, 2006(4): 58. Zhuge K. The academic value of "Art of Creation"[J]. 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2006(4): 58. (in Chine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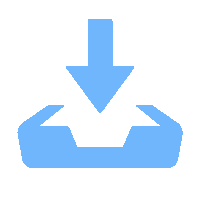 下载:
下载:










